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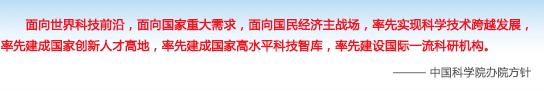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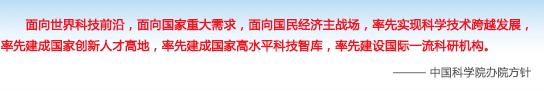
2020年,在中国居民的总消费支出中,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到77.7%。
同时,这一一状况正如谚语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风连阴雨 所言,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往往会碰头叠加。就当前宏观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四个:信念的不确定性、疫情的不确定性、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普通人常常通过既有的思维、认知模式和经验来理解未来的经济活动,而经济学家和商业高管们甚至会用高深莫测的数量化模型来预测未来的经济活动,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精英都很难做出精准的预测到未来的变化,而精英们在金融或经济危机预测等方面极其糟糕的表现,已经让他们的傲慢声名扫地[3]。另外一个确定性的是,如何应对这一冲击,尤其是统筹和兼顾防疫和增长这两种既互补又消长的复杂关系,是宏观经济政策重心所在。当然,除了未能对上面的信号保持敏锐外,一些其他的信号也影响到人们信念的更新。●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 与国内不确定性增大一样,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也在持续增强,并且被视之为一种极端不确定性。事实上,大流行的一些影响,如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之大是过去四十年所从未有过的,这就是确定性的一个事实。
再比如,因流动性和债务危机以及因非法和违规经营而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和企业集团,可能引发系统性危机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性影响,因而监管部门的接管行动有其必要性。而高增长所带来的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以及可预见的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成为地方财政收入和收入增长的支柱,从而在地方经济高增长——快速地城市化——房地产需求和价格的持续飙升——财政收入的强劲增长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相互加强的正反馈系统。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
而都市圈通常是指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大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础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为了解决城市房价飙升的问题,普遍实行城市住房的限购政策。随着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加快和城市绿色发展的要求成为硬约束,我国的大城市普遍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城市经济中的服务业占比不断升高,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发生深刻变化,工业和服务业在推动城镇化中的力量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五)城市中的巨大流动人口 城镇化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人口从乡村向城镇的集中,但巨大流动人口的出现,却也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甚至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
逆城镇化可以说有三个规定性:一是乡村人口的外流出现逆转,但农耕者人数可能继续减少。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中国的城市发展实践,似乎也在验证这种越大越好的想象。劳动年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也对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深圳,芝加哥曾创造了工业大都市崛起的神话,而深圳更是创造了工业大都市的奇迹,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人口超千万的大都市只用了20多年。二、我国推进城镇化面临的挑战 2021年我国城镇化率接近65%,进入城镇化中后期发展阶段。
然而,相关专家也发出警示,过早的去工业化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对于刚刚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工业化进程远未结束,工业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地位没有变化,工业的发展依然是推动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黄金30年期间,到处是大规模建设的吊车和脚手架,无数的城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工业对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而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和提供就业机会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三是乡村生活复兴,改变了乡村人口特别是乡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的乡村凋敝和衰落现象。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也面临着一些自身的突出问题。从1990年到2020年,可以说是中国城镇化跨越式发展的黄金30年。

而在1980年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2%,发达国家的平均城市化率达到70.2%。而在2020年制定的十四五规划(2020—2025年)中,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都被上升到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重要内容高度。
这些先兆包括:一是乡村休闲旅游人数增势迅猛,近年来每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游客达数十亿人次,形成几千亿元的消费,当然目前受到新冠疫情的很大影响。但是,由于城镇化的自身规律和中国城镇化的一些特有给定条件,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有时也并不完全沿着规划的最优轨迹行进,把握这些趋势对应对中国城镇化的挑战至关重要。现阶段中国的城镇化正处在步入高质量发展的转折点上,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城镇化的特征、挑战和未来发展趋势。一个是土地所有权的公有制度。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兴起,冲破了行政区划对跨域城镇化发展的束缚,同城化的发展也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是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定居和农耕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
其实,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在城市自身,城市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力需求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则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压力,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度是这种动力和压力的比较。从1978年到1990年,城镇化率从17.0%提高到26.4%,年均增长0.78个百分点。
但对中国来说,今后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指标,可能还不是城镇化率,而是城镇化的发展质量,特别是能否将大量农村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市民化,能否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这两个指标并轨,能否大幅度缩小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水平差距。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和在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上的城市社会融入,并防止一些乡村走向衰败和凋敝,成为落实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在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城镇化在把握机遇和应对挑战中的选择,也将成为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德国在1890—1900年的10年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
但那时,乡村常住居民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不再是农民,这些乡村外来人员将成为推动乡村生活复兴的重要力量。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来说,城市生活成为国民生活的常态,城镇化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热门话题,人们更多的是在谈论城市病。2020年,中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3.9%,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才只有45.4%,这两种城镇化率相差的18.5个百分点,意味着全国还有约2.6亿在城镇常住的农村户籍人口,其主体是在城镇工作生活半年以上的农民工及其亲属,他们还没有获得城市户籍以及相应的福利待遇,没有实现真正的市民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2亿人,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33亿人。
经济学家的解释是,中国作为一个脱离温饱阶段不久的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升级遇到了门槛,在教育、文化、媒体、医疗、保健、住房和体育等一系列新兴消费领域,都还没有形成有效消费的供给体系。我们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相关研究来解释这种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是否会导致中国城镇化进程和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放缓。
当然,对于中国来说,人们对新型城镇化也具有一种期待和厚望,即城镇化能够继工业化之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中国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但与欧美城市化过程相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这就使得中国城市中60岁以上老年人中的实际不从业人员的比例相对较高。二是由于大城市的生活成本高昂,从大城市到乡村异地养老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各地气候宜人、舒适安逸的乡村和小城镇,以及越来越多的康养中心涌现。
但中国作为人口众多、人口密集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医疗资源远低于发达国家,一旦疫情大规模扩散开来,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对具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和缺乏医疗保障条件的弱势群体来说更是致命的。从2010年到2020年,城镇化率从49.7%提高到63.9%,年均增长1.42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中国的这种特殊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和流动有序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和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特别是导致巨大的城乡发展差距,而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软肋。城市经济的聚集效应,成为城市快速发展的主要诱导因素和推动力量。
(五)城镇化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的新阶段 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快速发展的中后期,尽管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增大,但城镇化动力仍然强劲,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能。社会学家则更加强调收入差距过大对大众消费的抑制作用,呼吁促进中等收入群体成长、建设橄榄型社会。
新冠疫情防控带来的物理空间隔离,大大增加人们对互联网的依赖。其实自1998年以来,中国一直强调扩大消费的政策。
然而,庞大流动人口的出现,也存在城乡分割管理的户籍制度的原因,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随迁亲属,难以转化为享受城市居民同样待遇的市民。但由于此后大跃进和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特别是文革期间1000多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镇化长期停滞。




© 1996 - 2019 君圣臣贤网 版权所有联系我们
地址:茶亭东街